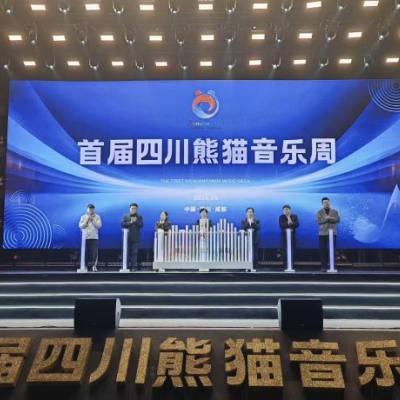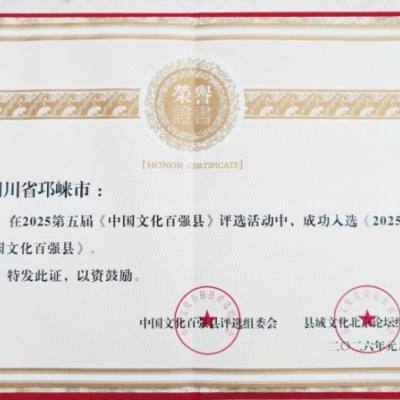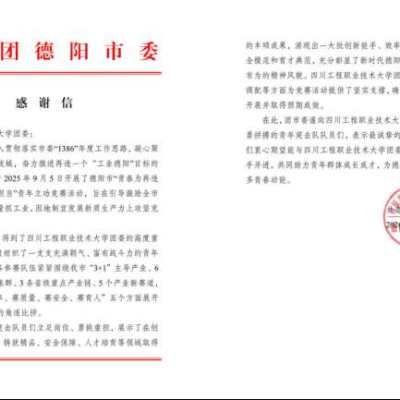■ 王超
李启贵参加工作30多年,从来没有离开过泸州炭黑厂,成为了目前“最土著”的泸炭厂人。 多年来,李启贵凭借自己的努力,从技术员一路成长为副厂长,个别年龄偏长的员工看在眼里,但心里总是不服气,原因竟然是他们认为:这个领导不懂生产。
领导不懂生产,那怎么行。不知几时起,这句子虚乌有的“不懂生产”成了标签,贴在了李启贵的“背后”,印在了李启贵的心里。
李启贵大学毕业后“子承父业”选择了炭黑生产这一行当。 那时的泸州炭黑厂经营规模和行业风光羡煞旁人。 认领师傅后,李启贵开始了自己的事业,从一开始的发电车间水分析到甲醇工程筹建组,再转岗到炉黑车间,中途提升到生产技术室管理了几年工艺,然后一直做到炉黑车间副主任,再又回到生产技术室担任副主任。几经波折的李启贵,岂能是几个阶段能概括,眼看仕途总算拨开云雾见太阳了,可是企业已经面临“关停并转”,泸州炭黑厂没了编制,还依旧要生产运行下去。
这样的情况维持了9年,确因泸州炭黑厂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市场需要,2009年西南油气田公司正式为泸州炭黑厂组建编制,对管理性质也做了相应的调整,成为中国石油旗下唯一的炭黑生产厂。
2012年,组织有意提拔李启贵,还在“吹风”期间,有人开始在背后搬弄起是非,认为李启贵不熟悉炭黑生产,不懂生产。流言蜚语传到李启贵的耳朵里,但他不敢做声。因为刚刚恢复编制的泸州炭黑厂,经受不起任何影响稳定的问题。
“在那期间,我整夜、整夜地睡不着觉,不停地反思自己的人生。”为了照顾好员工的情绪,一心只想抓好生产技术的李启贵只得装聋作哑,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让谣言不攻自破。
国内冶金用炭黑在1982年之后才开始慢慢量产,但因质量不高,只得用于普通合金和冶金行业。高端硬质合金生产用的炭黑,还是依赖进口。
2000年,实施关停并转的泸州炭黑厂所属甲醇、甲醛、橡胶、翻胎、发电等等项目统统歇业,资产变卖,仅留下炉黑车间和一条炭黑生产线。近千名员工选择离开,仅100余人回厂继续组织生产,哪有心思提高质量,可谓内忧外患集一身。
“不创新能吃几年老本?”工艺老、装置旧,半补强、冶金用两种品质的炭黑产品共用一条生产线,技术方面也许没有捷径可走,是否应该在辅助环节上动点脑筋。在担任工艺技术干部时,李启贵并没有因为人微言轻就混日子。
生产规模和经营性质突然改变,对李启贵并无影响,他一心钻研着怎样把水做纯,可以提高炭黑的质量,甚至将废水回收。
过去,日产污水数十吨,这个问题也成为李启贵攻克的课题。他开始分析每一批次的产品检验结果。没有技术思路,硕大的装置,各种化学品、罐剂、机泵尤如破铜烂铁。丙酮高是什么原因?灰份指标如何提升?几年间,李启贵始终将生产前端、后端一起盘算,在自来水厂学经验,找同行要技术,最终利用原甲醇车间的旧设备建成化水站,把生产废水,全变成了“超纯水”,炭黑质量也得到大幅提升,推出了和欧洲产品媲美的“高纯冶金用炭黑”。
解决问题一身轻松。2011年,李启贵取消半补强炭黑生产,全力生产冶金用炭黑的建议获得采纳,虽然生产成本非常之高,但泸州炭黑厂的产品质量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。同年,该厂年产量达到1100吨,超出了单一生产线最大产能10%。
岁月不居,时光如流。转眼间,泸州炭黑厂60年了,李启贵也55岁了。
去年12月在玉龙苑家属区,一位姓谭的老同志路过泸州炭黑厂机关楼,冲着楼前穿着红色工衣的人群说:“单耗创出近10多年新低,产量也是7年来最高的,装置这么旧了还得行,你们真是凶噢!”
“凶”,是因为大家心系生产。“凶”,也是因为以李启贵为代表的炭黑人一直没有放弃。
去年11月底,装置检修完成并投产后的第一天,天还蒙蒙亮,心里有些不踏实的李启贵走出小区,来到离厂区不足500米的地方,抬头定睛一看,一坨形似黑烟的云,笼罩在生产区域上方。
“不好,装置有事!”李启贵三步并两步,一路喘着粗气,跑到了主控室。
“你们在干啥子?!”
经过排查,原来是主控人员粗心大意,所幸发现及时。“这一股黑烟要是升起来,那还得了。”扶了扶眼镜,李启贵严肃地对操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。
老装置一直“抱恙”,生产稀稀拉拉不稳定也让他们头痛。就在去年拉网式排查生产问题时,李启贵“脑洞大开”,突破性地提出建议,并找到了困扰已久的症结,让生产真正的稳定至今,员工们纷纷为李启贵竖起大拇指。
“解决了这个难题,我睡觉也安稳,在面对员工和退休老同志时,我也能挺起腰板说点响亮话。”李启贵由衷地笑出了声。